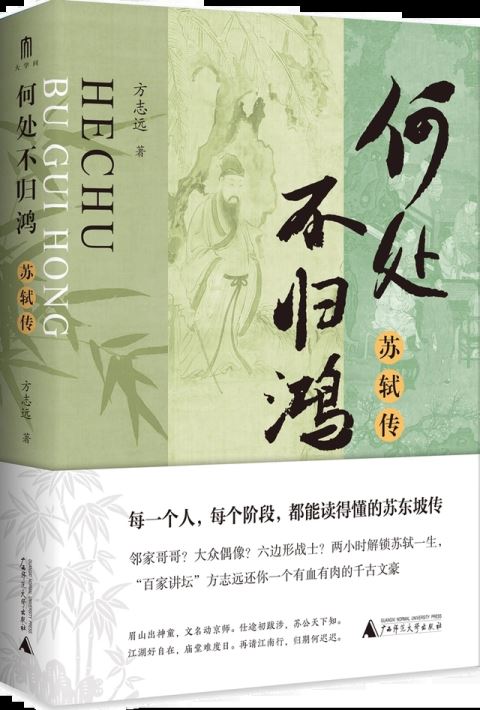
《何处不归鸿:苏轼传》
方志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1月
□禾 刀
苏轼以诗词闻名于世,写苏轼必然不能绕开他的诗人身份,不过他的历史形象理当更加丰满立体。“百家讲坛”主讲人、著名文史学者方志远以苏轼的生命过程为经,以苏轼在不同时期展现的才华以及仕宦经历中体现出的精神内核为纬,串联起其诗、其文、其词,其书画、其美食、其养生,体现其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抱负,以及作为普通人,在爱情、友情、亲情等方面的朴素情感,重点刻画其在面对仕宦沉浮时由彷徨恐惧到豁然旷达的心路历程。
苏轼虽诗词早负盛名,但让他名气大震南北的,无疑自黄州开始。“乌台诗案”事发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团练副使是宋朝专门用来安置被贬文官的十等散官之一,职务低微且无实权。该职薪酬本来就低,苏轼因被贬而只能半薪,养活家人困难,只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好在黄州太守陈君式仰慕其才华,将一块坡地划给苏轼。苏轼倒也入乡随俗,带领家人垦荒种地,并自号“东坡居士”。黄州期间,苏轼写下诸多名篇,除了前面提到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更显人生豪迈豁达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虽三次遭贬,但苏轼心性旷达,每次都乐观以对。初贬黄州时,他在垦荒种地的同时,不忘以诗会友,广结志同道合之人。再贬时苏轼一路五次降职,很快忘却一路旅途艰辛和刁难,脱口而出,“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三贬儋州,在当时,此地仅是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当时的儋州,贫穷落后,条件比以前两次贬所更差。尽管如此,苏轼却以“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将儋州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很快便入乡随俗。
今人回忆苏轼,主要是他那耀眼的诗词光环,其实,苏轼无论在政见,还是为政一方时,均勤勉务实。苏轼不唯上,不唯虚,只唯实。虽然他敬佩王安石的为人,但他对王安石的新法并没有因敬仰其人而不问所以,反倒对“乡试取举人重德行而略文章”持质疑态度。任杭州通判时,他发现不少人因贩卖食盐而身陷牢狱,于是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新法食盐专卖之制理想虽美好,现实却很骨感,为此他上书直指其弊,哪怕得罪宋神宗和王安石。
苏轼多地任职颇有政绩。被贬颖州(今安徽阜阳)时,他组织兴修颍州西湖大堤;任杭州通判时,他与知州一起,对当地年久失修的六井进行修葺。后再次来杭州任知州时,又反复上书争取朝廷资金支持,疏浚了西湖,筑成“苏堤”,“苏堤春晓”今天已成西湖著名十大人文景观之一;被贬惠州时,他出钱出力,疏浚西湖。在任徐州知州时,面对黄河决堤,徐州大水围城,苏轼身先士卒,带领当地军民奋战七十多个昼夜,成功保住了徐州城。在仕途最后一站儋州,他兴办学堂,为当地百姓称道……
苏轼每到一处,入乡随俗。所以,苏轼既不乏朋友,也不乏民众拥趸。正因如此,本书特别对比了苏轼的主要政敌章惇。“章惇无论在朝在野,自己总是如箭在弦,没有一天悠闲自在”。苏轼仕途不如意时既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苟且偷生,反倒脚踏实地,在坚守中追寻自我。
书本最后,作者用一幕广阔的“民意”场景,描绘了苏轼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苏轼重返中原的消息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传到了三川五岳,在雷州、在廉州、在梧州、在广州,在英州,在韶州,在虔州,在洪州,在金陵,处处有欢迎他的大众;有相识的,有不相识的,人人都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东坡居士的风采。人们不仅仅是为了他的千古文章,更是为了他的万载正气。”回顾苏轼的一生,旷达的性格造就了他不怨天尤人的乐观生活,而正气的坚守,驱使他既为民请命,又为百姓造福。从这层意义上讲,苏轼身上散射的,不只是诗词的光芒。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