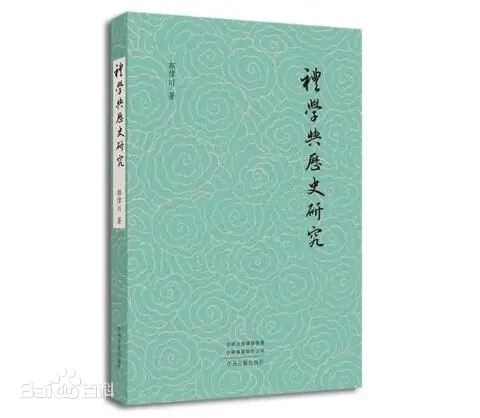
《礼学与历史研究》 郭伟川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23年3月
□黄少青
著名文史专家、学者郭伟川先生,在上古史研究专著《两周史论》和《〈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问世之后,《礼学与历史研究》是他推出的又一部新著。全书煌煌一百二十万字,内收《“礼”与礼学: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石》等学术论文近二十篇。又一次在学术界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飞先生,是对郭伟川先生在礼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有着深入了解的业内专家。借助他写在《礼学与历史研究》前面的《序》,或许是我们打开郭伟川先生此书的窗户,可以有所窥探的方便途径。吴先生在《序》中特别指出:“郭先生非常自觉地继承了自王国维先生以来的研究传统,一方面全面接受现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又不认可这些现代科学相对主义和伪价值中立的取向,而是以现代学术方式重新理解古经经义。”这是吴先生从古经经义研究传统的高度对郭伟川先生的研究方法加以考察而后得出的精准评价。吴先生还指出:“郭先生不仅在礼学研究的思路上非常接近王国维,而且其判断也与王国维相似:礼乐文明是肇端于周公制礼的。”这所谓接近和相似的判断,实则表明,郭伟川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为有源头活水来”,庶几堪与王国维媲美。吴先生进一步指出:“就对礼制和礼学的实质理解而言,郭先生帮助人们逐渐可能走出朱子以来,只能狭义地理解‘礼’的思路。礼,不止于揖让进退,冠昏丧祭,连国家的官制和根本大法,都是礼学的范畴……这也是郭先生将礼当作中国文明的基石的另一层含义所在。”这对于郭伟川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首肯,意味着远非一般研究成绩可比拟。据此,可知郭伟川先生在上古史礼学研究的学术高地上,是戛戛独造的一个,并且营构了一片可以引人入胜和饱游饫览的新风景。
具体从《礼学与历史研究》中的第一篇《“礼”与礼学: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石》和第二篇《中国“古典礼学”研究初论》,郭伟川先生于前者给“礼”下了定义,认为“‘礼’是个人自处和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也是人与自然包括天地鬼神之间应对之道”。对此,吴飞先生指出,这是郭先生“试图在中外比较以及社会文明史的梳理中,为中国礼学定”。郭伟川先生宏大的学术格局,也由此透示了出来。后者则由郭伟川先生提出了“古典礼学”的概念,而暗示必有与之相对应的“现代礼学”的概念,因此在吴先生看来,郭先生是“以礼学的概念贯通古今”,乃“发前人之所未发”。当然,这也是郭伟川先生深具学术识见并且不脱离时代治学指向的重要体现。
书中《先周时期的官制、礼制与古代国家文明》和《孔子儒学的南传与子夏的西播》两文,侧重点各有不同,前者诚如吴先生所言,是集中考察古代官制,后者则是对子夏学派与魏文侯关系的讨论,它们都是郭先生对其专著《〈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的补充性研究。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结合阅读该专著的话,那么对郭先生在这项研究上的考证论述,将会进入更深层次一点的理解。如从后者的内容大略可知,孔子一生崇慕周公并继承其礼治思想,在楚国约半年以上的讲学,产生的影响并不小,学生子夏在他去世后,继承其遗志,继续传播儒学,而魏文侯则是春秋战国之际最为尊儒好古的国君,因此,子夏与魏文侯的契合,与西河学派的创立,使孔子生前西行传学的愿望得到了实现。这都是儒家礼学发生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事件。
《礼学与历史研究》中其余诸多篇什,大致都从不同角度并依据不同的文献资料,围绕着礼学的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和观点的表达。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生前对郭伟川在礼学研究上的努力给予了非常切合实际的评价。饶公说:“余素主张史学出于礼家,史公著《五帝本纪》,取之《大戴礼》斯其明征。郭君伟川颇韪余说,扩大其论及于全史。顷读其新著《儒家礼治与中国学术》,张皇幽渺,大有助于史学。”郭伟川先生自己则言,他研究礼学,重点在于“礼治”。他认为,孔子所指的“礼”,是“包含国家、社会、群体、宗族、家庭及于个人的各种典章制度、宗法制度和个人守则”,即所谓“礼治”。应该说,这是吻合于中国历史的。
与此同时,我认为,如果我们再把国家上古史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在郭伟川先生《两周史论》的《序》中的一段话拿来参照阅读,则对于郭伟川先生在礼学研究上的理解,也会有所增加裨益。这里不妨将其抄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尾。李学勤先生说:“实际上,郭伟川先生对‘礼治文化’的阐述还不限于两周……特别是论宋代理学一文,认为‘儒’发展至此一阶段,已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儒家礼治所建立的典章制度和社会秩序已基本完型,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也受到世人服膺。所以,儒家礼治观念所建立的客观世界已趋于完备,换言之,礼学至此已没有多少可以发展的余地。因此,儒家至此一阶段,只有向主观唯心哲学方面发展,因此以儒家的心学、佛教禅宗之心学与道家的天际理论互相会通,而主旨在于阐述儒家经学并进而令其哲理化,这正是宗代理学的特色……最后通过对朱熹集注《四书》的肯定,使社会的政治文化又重新纳入儒家礼治的轨道,此乃宋代学术的归结所在。这一看法确实相当重要,启人深思。”这表明,肇始于两周而向下延伸而来的儒家礼学传统,是郭伟川先生的礼学研究所涵盖的历史上下文。故而李学勤先生说:“我们期待郭伟川先生继续扩展他的工作,对中国的礼学研究有更多贡献。”作为读者,我们也存在着一样的期待!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