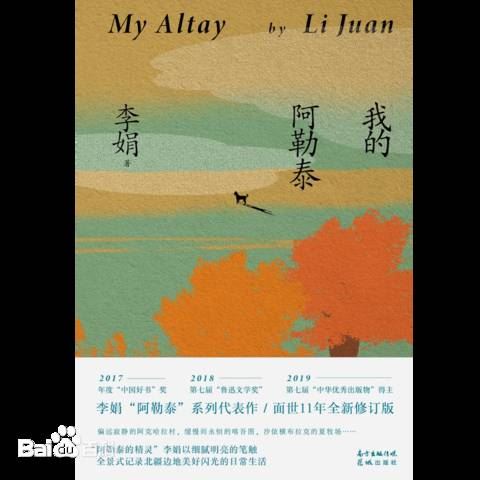
《我的阿勒泰》
李 娟 著
花城出版社
2021年8月
林晓兰
当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也成为我的案头书时,对新疆的向往与想象,在这个夏天也变得前所未有地强烈起来。只是,每每念头掠过之后,我却一次次地问自己:我究竟要把李娟与她的《我的阿勒泰》读成了哪一种版本:是文艺清新的“诗与远方”、还是面对“眼下生活苟且”的乐观、还是……这一切,对我来说,还真的是一场未知的阅读之旅。
在阅读完书中第一辑“记忆之中”那11篇叙事性较强的散文之后,作者对现实举重若轻诙谐幽默的记录或书写时,刚开始,真的不明白身处恶劣环境中的作者于字里行间的从容自信、四两拨千斤的娓娓道来中,那时不时流露出来的诙谐底气,究竟来源于哪里?比如在《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一文描写我们为了省钱,而坐着叔叔开的摩托车去县城的一路上所遭受的罪:“……于是出一趟门总得吹四五个小时的风,可真够受的……头盔兜着满满的风使劲往后拽,拽得头盔的带子紧紧勒着脖子。勒得人头晕眼花还吐着半截舌头。没一会儿,门牙就给吹得冰凉干涩。”
“中途休息的时候,对着车上的后视镜看了一眼,吓了一大跳——发现自己少了两颗门牙!再定睛一看,原来是门牙变成了黑色的了……”
诸如此类“苦中作乐”的书写风格,在书中更是俯拾皆是,难怪有人称李娟为“段子手”,但我知道,这绝不是作者为博眼球而有意经营的“亮点”,相反,越读到后来,越是时不时不由自主地想起历代文人的身影,她与他们太相像了!比如大家都熟悉的苏轼,在遭受仕途上的一系列打击之后,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里,面对这一切,这个在世人眼中简直就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最终还是把“随遇而安”演绎到几近“完美”的状态。李娟,从她幼年到青春一路走来所经历的艰辛与苦难,虽无法与苏轼宦海沉浮的“浓墨重彩”相提并论,但如果与同龄人相比,年轻单薄弱小的李娟,所走过的每一步,对她来说,又何尝不如于荆棘上行走的疼痛与苦难?幸亏,中国文人身上那种即使身处苦难困境却依然积极乐观的精神基因,最终还是流淌在李娟的血脉里。故而,新疆之于李娟,也让人想起杭州之于苏子。当读到第二辑“角落之中”(于2002年-2006年创作的)的篇章,我们也恍若看到了北疆的那片风景,正在李娟的灵魂里无限地打开,给予她生命中前所未有的明亮色彩:“春天的天空总是斑斓又清澈。云雾来回缭绕,大地一阵阵蒸腾着乳白的水汽。春天的空气仍然非常寒冷,但和冬天不同的是,春天的寒冷中有了温暖的阳光。而冬天的阳光,更像是一件银器散发出来的光,没有一点热气。”
又比如在《喀吾图的永远之处》中描写春天来了那种美得让人物我皆忘的场面:“河水暴涨,大地潮湿。巨大的云块从西往东,但低地,飞快地移动着。阳光在云隙间不断移动,把一束束明亮的光线在大地上来回投射。云块遮蔽的地方是冰凉清晰的,光线照射的地方是灿烂恍惚的……”
我们都知道,居住在新疆的那些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李娟在《乡村舞会》一文中对于那些舞蹈着的生命,更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美到极致的美写:“他兀自在喧闹的、步履一致的人群缝隙里入神地扭肩、晃动双臂,又像是独自在遥远的过去年代里那时的人们狂欢……音乐只在他衰老的、细微的、准确的,又极深处的感觉里。舞蹈着的时光是不是他生命最后最华丽最丰盛的时光?”
还有少女对麦西拉那份纯洁而又无望的暗恋,也是美得如此令人心碎:“他温和平淡地坐在房间嘈杂的漩涡中,安静得如同旷野一般。那琴声一经拨响,就像是从不曾有过起源,也再不会结束了似的,一味深深地、深深地进行着。音量不大,却那么坚定,又如同忠贞……”
毫无疑问,正是北疆那片土地给予了李娟美与爱的精神盛宴,才让她的生命与灵魂在被滋养了之后和那些无比明亮美好、无比辽阔深远的万物,一同茂盛葳蕤有力起来,而这又何尝不也在有意无意中奠定了李娟后来行文日趋从容淡定、积极乐观、甚至开始走向对现实的思考与批判悲悯同在的精神底色?《木耳》的描写,便足可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文中作者写了她们一家如何艰难地采木耳、收购木耳、贩卖木耳以谋生,到后来因为大家发现木耳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自此,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采到木耳、甚至采摘挖到其他值钱的山货,开始不惜破坏山林、疯狂掠夺的行径,最终,导致了瘟疫的暴发、再到后来山林被毁、木耳也彻底消失了……
“木耳没有了……生活还在继续,看起来只能这样了。但却是永远不一样了。更多的事物分秒不停地到来,并且还在加速。最巨大的变化就是种种巨大的变化都开始无影无形,几乎无从感知。”
作者借对“木耳”的消失的悲伤缅怀,来表达出对一切古老、原生态美好的“没有”(消失)的无比怅然忧伤、甚至无声的愤怒无奈,又何尝不是在无形中揭露了人类在利益驱使下的种种不堪?在这里我们便不难看到了一个“文艺清新、积极乐观”之外、于思考与批判中又不乏悲悯情怀的李娟,正从阿勒泰向我们有力地走来……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