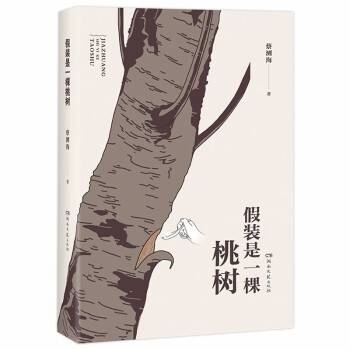
《假装是一棵桃树》
蔡测海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年10月
□禾 刀
“端午节那天,父亲来到学校。他那样子,一看就是个爹”。在《父亲简史》这章里,蔡测海这话既直白又深奥,一看就懂,但又意味深长:到底什么样的样子,才能一看就是个爹呢?想必答案装在每个人的心中。在《假装是一棵桃树》中写到农村知识的贫瘠时,一只没了电的手电筒,被他写出了恍若隔世的历史隔膜,“我不知道换新电池,以为它死了,机器也有寿命”。《牧歌》里写“和父亲争吵,两个人一天没吃饭。生气可以当食物,生三天气,等于多种一丘田。一直生气,你就是一座粮仓”。司空见惯的家长里短,经蔡测海三言两语,顿时变得如此诙谐,如此深刻。
《假装是一棵桃树》一书是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蔡测海三川半系列小说的汇编,全书共辑短篇小说23篇。蔡测海的这些文章内容丰富,大都取材于身边人身边事,他写了知识对权势的憎恶,写了支援三线建设的热血沸腾,写了外公解放前的特殊经历,写了渡船姑娘用“正”字渴盼心上人归来的动人故事,写了父亲的土匪经历……通过多种人物叙事,三川半风土人情的拼图日益丰满。按照蔡测海自己的解释,所谓三川半,指的是湘鄂川三省交界处,那里是他的老家。地理位置决定文化场域。三川半历史上虽偏处一隅,但仍屡遭兵燹,为糊口饭吃,有的人跟着队伍跑,后来才弄清各路队伍到底是怎么回事。
蔡测海的文章一直独树一帜,既像散文,又像小说。他的文章就像是打开另一个神秘世界,不拘泥于传统叙事,语言简短怪诞,跳跃性极大,必须细读深读,初读难察,细嚼意味深长。他不在意套路,文字都是他天马行空的信意行走。有时读来似觉费劲,放下对内容似乎所记不多,但脑海深处又死死地认定他的文字直白深刻。有时眼前不经意间会跃入几行字,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如“跳房子的格子里是我,教室的格子里也是我。这许多格子,有的装着约束和理想,有的装着自由和快乐”。跳房子大抵是农村过去小孩的常见游戏,蔡测海从这种格子与教室格子对比中,悟出“理想”和“自由”,像是另一种“格物致知”。
三川半是蔡测海深耕乡土底层的窗口,许多细节世俗而又别具韵味。“我们乡下人,会在街市认一两门亲戚,有面子,赶街讨碗凉水喝”(《河东街事》)。喝水事小,展示这层关系事大。他对乡土怀有深深的情感。在《荒路》中:“几个屋场的人,一夜之间都搬走了。那些大屋,慢慢朽烂,瓦一片一片掉下来,后来房屋一齐倒塌,像山崩。老屋场变成地名,主人的姓氏藏在地名里。”热火朝天城镇化的背后,被掏空的乡村日益破败凋零,许多老屋因人走屋空,乏人维护,耐不住风吹雨打,倒向大自然的怀抱。而地名,是过去记忆留下的最后倔强。笔者老家的村名,据传就来源于近千年前的岳飞抗金屯兵之所。
蔡测海对三川半乡野历史的打捞,力求平实。乡村里的人大都有晕名(即绰号),像猪鼻孔、四眼、刘驼子、吴矮子等等。须知,晕名并不一定就是歧视或者敌意。曾在农村生活过的笔者至今还记得发小赐给本人的晕名,但搞不清来由。晕名体现一个人的特征,这种特征或是生理性的,或者缘于日常生活的归纳,但无一例外相当精准。乡邻对晕名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前提是必须尊重辈分。
在乡下,有的人直到离开才能唤醒人们的关注。猪鼻子离开后,人们陡然发现生活中似乎突然被打开一个缺口,少了点什么。蔡测海笔下的人物朴实无华,没有任何粉饰,对他们的那些过往无论亲疏是非,都是原貌呈现。或者说,他摘掉了那些尘世中的伪善面具,还之以本真:三川半的人们可能没有高大上的鸿鹄之志,但他们更在乎的是满满的烟火气息。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