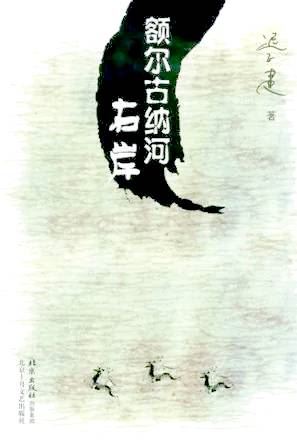
《额尔古纳河右岸》
迟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10月
陈佾生
与其说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长篇小说,莫如说它是一首长诗,或者说,是一章长篇散文诗,它吟唱的,是一曲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赞歌。作品用诗的意象和诗的语言演绎爱情和生死这两大主题。
鄂温克族的孩子,从小在希楞柱中听惯了父母夜间制造的“风声”,“风声中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亲的呢喃”,成年后,他们自己也与所爱的人制造类似的风声。正是在这样的风声中,一代又一代新生命诞生了。爱情是美好的,生命的繁衍是圣洁的,因为它们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是人类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最具活力和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所以是值得用诗一样的激情加以赞美的。正因如此,在作者笔下,“我”与拉吉达的鱼水之欢才如诗如画,美得让人心醉:“在那个动人的缠绵的过程中,我一直看着天上的云。有一片白云连绵在一起,由东向西飘荡着,看上去就像一条天河。而我的身下,也流淌着一条河流,那是女人身下独有的一条暗河,它只为所爱的男人涌流。”当年与弟弟林克同时爱上达玛拉,却在兄弟俩以射箭比赛争夺爱人时故意射偏,退出竞争的尼都萨满,在林克死后花两年的时间用山鸡羽毛缝制了一条精美的裙子献给达玛拉,并深深打动她。可惜他们的爱情因不被族规允许而夭折。但是,这件尼都萨满用心血连缀而成的羽毛裙已成为爱情的象征,艳美绝伦,它像彩虹一样缤纷明亮,不但照亮了达玛拉的心房,而且照出尼都萨满的真爱和高尚人格。
鄂温克人一辈子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与疾病和饥饿作斗争,风雪、野兽、外敌、瘟疫、疾病……灾难和死亡的魔爪随时伸向他们,但他们都勇敢面对,坦然视之,表现出令人钦敬的勇气和智慧。在鄂温克人眼里,死亡并不可怕,他们认为“人离开这个世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了。那个世界比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要幸福”。为部落外出换取驯鹿遭雷击而死的父亲,“他的灵魂一定隐藏在雷电中,发出惊天动地的光芒。”马粪包因亵渎神灵被熊骨卡住喉咙,差点儿没命,妮浩萨满跳神救下他,他吐出的熊骨,“看上去像上天扔下的一朵玫瑰。”为救马粪包,妮浩萨满献出了女儿交库托坎幼小的生命,妮浩的神歌唱着:“你落了,太阳也跟着落了,可你的芳香不落,月亮还会升起!”献给女儿一曲生命的赞歌。鄂温克人认为,人类向大自然索取,必然要付出代价;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作为与自然平等的个体存在。灵魂回归自然的方式是对其生命最具诗意的阐释。
作品中多次描写萨满为救人而跳神,渲染神的灵异与神奇的法力,被认为是虚幻和荒诞的笔法,因此招来诟病。对这股超自然的“神力”,你可以看到“愚昧”,看到“落后”;我却看到敬畏和感恩,看到无私的力量,看到鄂温克人对生命无差别的尊重。妮浩萨满明知每救一人,她都要失去自己心爱的儿女,但仍义无反顾地操起法器跳起神舞——在她心里,救人是她作为萨满的神圣职责。鄂温克人,这支世代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民族,他们懂得,大自然是他们生命的土壤和源泉,所以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也把自己当作草木一样,是自然之子。正因如此,当我读到在伊万的葬礼上,两只白狐狸化作身穿素白衣服的俊俏姑娘前来吊丧,报答伊万生前对她们不杀之恩这一情节的时候,我一点不觉得荒诞和奇怪。在我看来,作者是把两只白狐狸作为一组意象,一组人与自然之间感恩与报恩、和谐相处的象征来赞美的。这种诗意处理的浪漫主义手法,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跋文中说“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的生存”。人类文明的进程,取与舍,开发与保护是一对困扰和考验人类智慧的矛盾。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生存、生活方式乃至所谓“愚昧”的民族文化,是否具有传承乃至弘扬的意义与价值?人类该如何与大自然共生共荣?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留给我们的思考。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