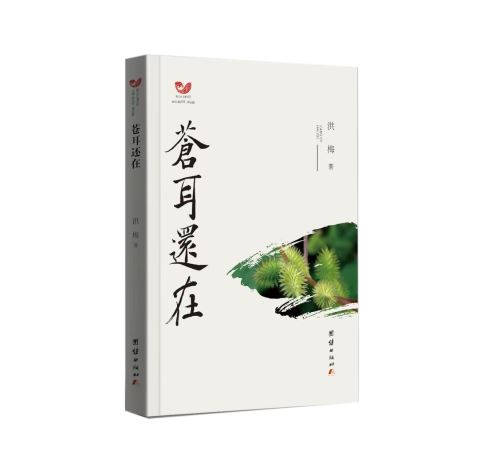
《苍耳还在》
洪 梅 著
团结出版社
2025年7月
陈泽楷
在广袤的潮汕平原上,有一种被当地人称作“虱母头”的植物果实,以它倔强的姿态刺破时光的茧壳,而这种学名叫“苍耳”的植物,如今成为文友笔下的别样风情。当洪梅将这本浸润着草木清香的散文集《苍耳还在》递到我手中时,我仿佛看见那些带着倒刺的小果实正粘着时光的味道,将上世纪70年代的集体记忆与个体生命体验悄然串联起来。这位与我相识十余载的潮汕女作家,始终以静水深流的姿态,在文字的园圃里培育着属于这片土地的精神植株。
我和洪梅相识于2013年我刚涉足本土文学圈的时候,迄今恰好是一个年轮。她为人低调、内敛,亲切如邻家“阿姐”,在文友中口碑甚佳。十余年的相知岁月,让我深知这本散文集的分量。散文集中的同名篇章《苍耳还在》,恰似一把打开记忆闸门的钥匙。洪梅以童年视角观察这种浑身带刺的野草,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苍耳既是孩童的小玩伴,更是连接故土的精神标识。
作为《学习之友》的资深编辑,洪梅的笔触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醒与温情,她在浩瀚的文本中捕捉最动人的细节,在平凡的生活里提炼永恒的诗意——《探访红树林的生命姿态》《时光里的长年羹》便体现了这种职业特性。书中最动人的篇章,往往浸润着潮汕文化的基因密码。《潮剧·乡愁》里,老戏台斑驳的木纹与演员褪色的戏服,在洪梅笔下幻化成潮汕人流动的文化图谱。当她写潮剧戏迷“潮剧是寒夜里的一堆篝火,他踽踽独行,借着这束微光走到历史的传说里去看看风景,完成了精神上的一次次跋涉”,文字本身便成了承托乡愁的器皿,这种深情书写,与她本人的性情形成共振;在《龙脊梯田,抒写在高山上的诗行》中,她将镜头对准梯田的褶皱,农民的脊背与土地的腠理重叠,汗水滴落处泛起诗意的涟漪,这种去精英化的书写姿态,与其低调内敛的为人形成统一,恰如潮汕工夫茶道中“茶三酒四”的待客之道,在谦冲自牧中顿见真章。
洪梅的文字魅力,在于她始终以谦卑的姿态贴近大地。就像她笔下的苍耳,不择地而生却自有其生存智慧,在喧嚣的文坛保持着知性的定力。在《有一种忠诚,写在山海之间》中,这种定力转化为对海警战士退伍季的深情凝视,她用编辑特有的叙事节奏,这种人文关怀便具象为海浪般绵长的情感力量。在《青篮千人墓:不能忘却的历史之痛》里,洪梅以史家之笔记录达濠古城的伤痛记忆,文字间没有廉价的抒情,而是在克制的陈述中透出历史的凝重。《生命承受的重量》中对革命先烈的庄重书写,恰是她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
作为“70后”作家群中的独特存在,洪梅的写作始终保持着难得的纯粹性,她用20年光阴培育的这株文字植株,终以散文集的形式绽放出独特的文学之花。在这个速生速朽的时代,她固执地守护着文学的慢火,用知性的光芒照亮那些被遗忘的角落。诚如她在后记中所写:“我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如苍耳,根植于脚下的阡陌,沐泽于故乡的清风,涤荡于灵魂的河流……身为草芥,心怀须弥,带着自己去见万物与众生。”草木生长自有其时,当我们在文字的密林里迷失时,《苍耳还在》带着土地的赤诚和向阳的虔诚提醒我们:故乡从未远离,记忆始终还在。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