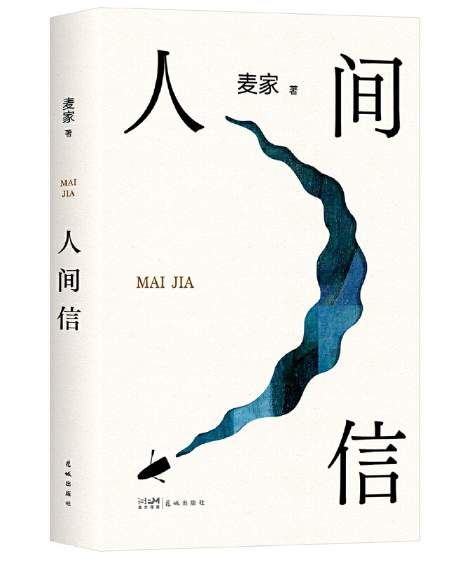
《人间信》
麦 家 著
花城出版社
2024年4月
□林 颐
“没人知道我小姑为什么寻死。或者,知道她为什么寻死的人历来闭口不言。”
麦家暌别五年的长篇小说《人间信》,以“小姑之死”开篇,以“我”的视角来讲述一个家庭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沉浮命运。这样的家族故事,在小说题材里并不少见。题材类似,那就看作家水平的高下,而麦家是个能从旧壶里倒出新酿的好作家。
这部小说的写作技巧,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叙事者人称的突变。
小说从“我”的视角切入,讲述的内容进行到大约2/3处,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父子冲突。 “我”为自己的尊严、家庭的荣誉而拼命,没想到,匆忙赶来的父亲,竟然不是帮“我”收拾仇家,反而对着儿子大打出手。于是,叙事者“我”一变而为“他”。
在接下来的讲述里,更大的风暴冲击着这个家。为了报复,为了证明父亲的不堪,为了获取母亲、奶奶这些家人对自己的偏爱,也因为身处的时代的价值观念的洗刷,为了表明自己与家庭切割的决心,为了赢得更好的前程,儿子揭发了老子,儿子把父亲推入了火坑。从此,“我”不再是我,“我”只能是“他”。一个异化的个体,一个放逐在家庭之外的、也只能自我放逐的、丢失了“我”的人。
后来,叙事者“我”又回来了。但是,读者可以感知到,这个“我”与起初的“我”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经历了社会运动的洗礼,在其中获得了如鱼得水的本事,获得了晋升的资本,这个“我”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我”很复杂,这个“我”代表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以人性的丢弃为代价,所以,“我”想回归,并不是容易的事。
很多人说《人间信》是一部“疗愈作品”,主题是儿子与父亲的和解,一封人间信,写给困在过去的我,由此从时间的捆缚里脱离出来,辨认出未被时间疗愈的伤口,由此“信人间”。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想,麦家之高明,就在于他跳脱了常规的“和解”场景。
父亲的死亡,很不体面,很烂污,恰恰注解了他被视作“潦坯”的一生,那种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不走正道、游手好闲的男人的一生。“我”对此的反应是——惊喜。父亲绝对是个混蛋,所以,“我”没错,“至少我原谅了自己。”请问,哪一种真正的和解,是这样的呢?
我与“我”和解,从此,放过自己了,关山无隘,可以轻松驰骋了。
在这里,麦家设置了一种更深刻的命题,是面向我们读者的问题:究竟怎样的“我”,才是值得原谅的?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我”的人生?
《人间信》的背景,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这个故事可以展开得很宏大,但麦家扣紧了“我”去写故事,用“我”的狭窄视角去框定故事的进程与范围。因为,他写的是“人”,写的是发生在“人”身上的故事。引发这些异化的,固然有社会的因素,但究其根本,还是在于人的本身,在于人性中的根弊。这关乎更普遍的、跨越时空的、亘古以来的,我们对“我”的追问,是对“我”的自我追寻。
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缺点的。爷爷的莽勇,父亲的自私,“我”的功利,都是造成家庭悲剧的根源。书中的女性们要可爱得多,以死驳斥重男轻女思想的小姑,作为家庭主心骨的奶奶,从无怨言全心奉献的母亲,把自己淬炼成老辣模样的小妹……人间破破烂烂,她们缝缝补补。可是,有时候,她们过于娇惯和包容,也助长了男人们的恶劣。所以,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突破时间限制的,在任何时刻都能引起我们思考的“我”与“我”相处的人生大书。
小说的语言清浅流丽。比如,小说开头写花儿与少女的类比,一个像蓓蕾一样的少女,不准备轰轰烈烈地去争奇斗艳,而要轰轰烈烈地去死。“我”对于这个花儿一样的少女(小姑)的眷念,象征了人性中对美好的向往,对命运不公的不屈抗争,而这正是铸造我们这部人类心灵史的所有渺小的“我”汇集而成的力量,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根本。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