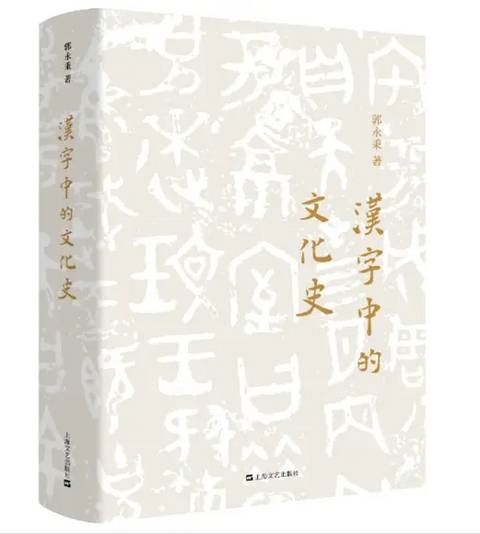
《汉字中的文化史》
郭永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4月
□赵昱华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承载千年文明的厚重历史。曾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不同汉字,可能多达三万乃至八万个字,但如今,我们常用的字不过六千五百个字。这六千五百个字,正是承载着我们文化的砖瓦,每一个字,都令我们与过往相连。
在这六千五百个字中,《汉字中的文化史》又精心挑选了九个字,放在历史学的视角下,以语言文字学为工具,延续着近九十年前陈寅恪等人所开创的道路——“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循字见人,由词观史,追溯千年前的文化背景。
在作者郭永秉挑选的九个字中,“中”和“国”二字是放在首位的,这充分反映了写作的目的,他挑选的这九个字,是为了解释一个核心的问题:何以中国?
“中”字本是指代一种充满神秘学色彩的事物的,或为旗帜,或为“天地中和之气”。“中”这个字,从旗帜变为方位,正是因为旗帜有着号召天下,令四方来从的意象,在作者看来,这样的转变,代表了古人赋予这个字的原始图腾性,这是一种普适性的价值观——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的同心共德。
居中而建郭,最早的“中国”一词,出自《尚书·梓材》,在此时,“中国”一词并非国家的指代,而是代表了一种原始的天下观,指的是周朝东都洛阳所辖的“中域”,以此为天下的中心,周人得以辖御四土。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周人设此辖域,是出自政治与文化的双重目的——政治上,周人贴近了各方诸侯,得以实行更有力的管控,《史记》所载的“四方入贡”,正是建基于此;而文化上,周朝原为小邦,缺少统御四海的合法性,而周成王于中域“宅兹中国”的举措,为周朝对四海的统治赋予了法统上的正统性,这份正统性,正是源自古人对“中”的重视。
作者用同样的笔法,通过“夏”解释古人的历史观,通过“天”解释古人的世界观。在我看来,这样的解释,实则是为了解释古人思想的来源。然后,作者旋即从“儒”“礼”“法”这三个字中,挖掘了古人思想形成的过程。
儒、礼、法,三者密切相连。礼,不是儒家的独创,作者引用朱熹的解释,发掘了“礼”与“履”之间的关系:“礼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作者据此解释,指出“礼”的概念不止于礼经的教条,更是对举止规范的履践,而儒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乃是赋予了“礼”这个字的儒家人文内涵。
礼和法,都是统治者巩固自身地位的工具,“礼”的起源是对举止的规范,而“法”的起源,则源自对神明的畏惧,“天意”赋予了法的正当性,而“天意”又随时间的发展被“人意”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神判法被习惯法所取代,再进而演变为成文法,但“法”的神圣性从未消解,反倒让早期神判法中裁决是非的牛羊,被神化成为了神兽獬廌.将“礼”与“法”,编撰成“册”,以此御“民”,便形成了早期中国的统治架构,到此为止,作者已经成功地通过九个字,完成了对“何以中国”的解释。作者把“民”放在了最后,并非对“民”的忽视,而是恰恰相反地把民众放在了历史的视角里面,这既是为了批判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在展望着未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这句话,是全书的引子,作者以此引出了我国古代的御民之道,作为暗线贯穿全书,但作者却又在此对这一家长制的统治形式进行了批判,引用陶行知的疾呼,向社会与教育界发出了呐喊,这种呐喊,是对过往的扬弃,他所呼吁的,是民众的主体性,是对未来崇高的企盼。
中、国、夏、天、儒、礼、法、册、民,借助这九个字,作者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合上书本,我想起维特根斯坦说过:“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旧日的许多事物虽然难免化作瓦砾,但瓦砾并不意味着破败,对这堆瓦砾的扬弃,让前人真正的精神得以流传,坍圮的瓦砾于是重构成为了我们陌生而又熟悉的文化。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