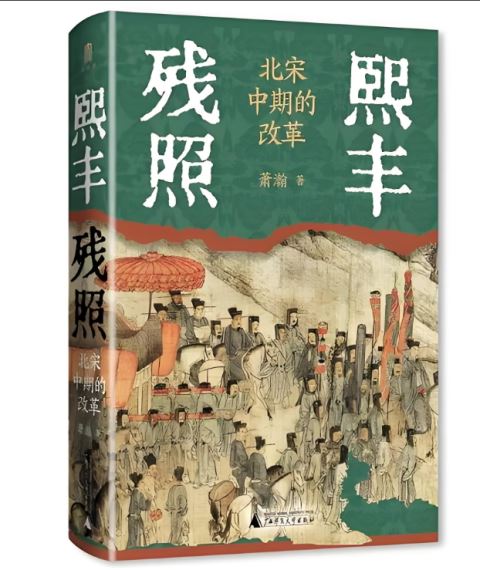
《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
萧 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赵昱华
北宋熙丰时期的变法(即王安石变法),向来是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在这一问题上,已有着诸多先贤高屋建瓴,作了多角度的思考与分析。这部《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的特点在于,把熙丰变法放在一个超脱宋朝的时间轴上,以更宏大的视角去分析其独特性与超前性。
作者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或许正是出于专业的素养,作者对于熙丰变法中各项改革措施的具体法令、制定时间、效果与演变等内容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进行了抽丝剥茧、逐条剖析的细致梳理。
在有关熙丰变法的具体事件与人物的描述上,作者采用了夹叙夹议的笔法,一方面以时间为序,对改革的全过程进行娓娓道来的叙述,另一方面则关注具体人物在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了哪些具体的作用,由事及人,再由人复归于事,对于变法中新旧两党的激战过程作了细致的梳理。
可惜的是,在评价具体人物之时,作者预设了立场,以“新”为正确,以“旧”为错误,认为支持变法就是道德高尚,反对变法便是品德败坏,这样的论断,显然难以服众。个人认为,对于角色的评价,应该减少主观上的道德判断,只需说明这一角色在变法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反作用,将道德的判断交由读者。
社会科学的出身,让作者关注到了熙丰变法与宋朝之前或之后南宋时期改革的不同——熙丰变法,在本质上是宋朝在面对自身“中期综合征”时的自救应对措施,这使得变法的实行有其独有的自觉性——作者将熙丰变法定义为在面对中国帝制历史的周期律时,对于封建皇权所打的一个“补丁”。我们应当承认,能客观认识到王朝周期律,并且对此作出有效反应,本身就是一种有先见性的行为。历史上的朝代,在面对自己的“中期综合征”时,往往或视而不见,或粉饰太平;能客观认识并反应的,也不过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一两例而已。
让笔者深受启发的一点,是作者对“为何‘旧党’要反对变法?”这一问题的解释。作者认为,很多“旧党”人士所反对的,并非变法改革中的具体措施,而是变法的其中一个副产物——君主权力的集中与强化。对于君权强化的反对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对旧有权力平衡被打破的不安,也有对自身地位下降的不满……原因种种,而反对新法实施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他们被笼统地归纳进了“旧党”之中,实则内部分歧很大。正是以“新”为正确,以“旧”为错误的简单逻辑,让他们彻底被推到了“新党”的对立面。既然如此,变法的失败与不彻底,便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可悲,可叹。
这也能解释为何在“靖康之耻”后,重建的南宋朝廷会将神州陆沉的灾祸归咎于“新党”。一方面,变法客观上提升了君主的权力,也使得君主的错误决策所导致的恶性后果加剧,系统性的纠错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当南宋实现了政局的初步稳定以后,君主集权的趋势非但没有有所收敛,反而被进一步加剧了。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士大夫群体尝试借由对“新党”“变法”的攻击指桑骂槐,经由这样的方式重建旧有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君臣关系,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讽刺的是,集权强化这一变法的副产品,反倒比变法本身的影响更为长远,不仅局限在这所谓的“熙丰残照”“绍兴中兴”上,甚至不仅局限在两宋时期,而是一路延传,直至皇权的巅峰。
阅读该书,熙丰变法的故事,值得为当下所警惕——改革的反对者所反对的,或许从来不是改革本身,而改革所造成的影响,或许也远不止眼下的这一时半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如这本书封底所写的那样:“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场无休止的历史对话,穿越时间的屏障,唤醒我们的反思。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