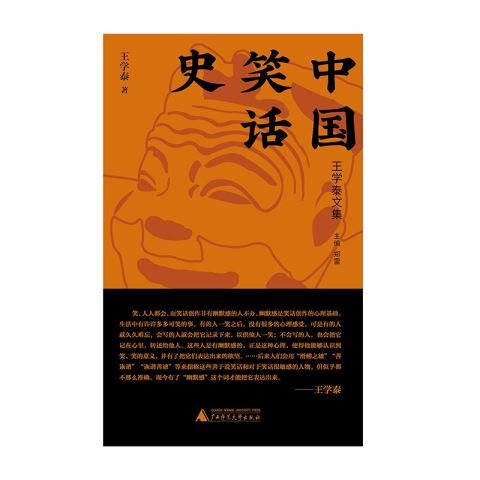
《中国笑话史》
王学泰 著
2024年10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禾 刀
笑一笑,十年少。一看到“笑话”二字,我们就会想起相声、小品、喜剧、吐槽、脱口秀等各种搞笑类语言节目。辟一清静之地,跟着王学泰回溯一下中国笑话的历史渊源,偶尔情不自禁地会心一笑,偶尔在品茗中又觉意味深长。
《中国笑话史》一书作者王学泰是著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曾出版《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等与笑话关联的著作。本书共分五章,作者首先以笑、笑话的基本要素、心理基础、概念等为研究开端,继而结合《诗经》《左传》《国语》《易》《汉书》《晋书》《史记》等史料,翔实整理了自西周至魏晋的中国笑话之萌芽时期、附庸时期和自觉时期的发展脉络。略感遗憾的是,本书只写到了魏晋至两宋便戛然而止。
经王学泰梳理可以看到,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笑话散见于《周易》《诗经》《左传》等少数著作里,那时的笑话大都以记事不记内容为主,偶尔有些记录的笑话也极为简略,很难撬动今人的笑点。不过,从本书列举的几则笑话依然可以看出,大都带有明显的嘲讽特征,有的还颇耐人寻味,如刻舟求剑和掩耳盗铃等故事。
在王学泰看来,先秦战国至东汉灭亡这一时期 “虽然有了笑话,但它还不独立,主要还是人们说明某一道理的工具”。但战国的笑话零星数量较此前有明显跃升,主因在各方势力为了合纵连横,无论苏秦、张仪,抑或公孙衍等人,惯用之术无非是奔走游说。“他们从民间采撷了大量生动有趣的故事,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用这些以吸引和说动人主”。如此一来,平日里那些原本难登高雅之堂的民间笑话,经纵横家龙飞凤舞地改造渲染,逻辑更加通俗易懂,表达更加脍炙人口。
还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客观上刺激各方在阐述学说观点时,必须绞尽脑汁吸引并说服对方。在谈到春秋战国的笑话时,王学泰提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爱讲‘宋人’的笑话”。王学泰分析后认为,这种偏好很可能与宋人身份有关,因为“宋国是殷族后裔建立的”,而“其他各国统治者多是周族之后”。强者取笑弱者,上官取笑下官,肢体健全者取笑残疾人,这在丛林法则占上风的时代几乎是一条铁律。
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书同文,车同轨,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不再,史料上记载的笑话数量随之断崖式下跌。王学泰很不客气地指出,“严格来说秦代没什么笑话”。汉代与先秦相近,具有某些承接性,笑话没有多大空间并不令人意外。
汉后,中国社会进入大混乱时期,长年的不稳定和现实的无奈,刺激文人以文化方式向思想深处寻找精神慰藉。王学泰称魏晋文化为“自觉的时期”。伴随魏晋文化的复兴,“笑话这种文体也逐渐摆脱了作为谈政论道的附庸状态,成为一种新的面对受众的独立文体”。其实历史上有着某些类似:战国时代群雄逐鹿,而汉代以后的大混乱时期,同样是各方势力竞相登场,又相互制衡,笑话这种带有嘲讽功能的艺术有了更多施展空间,有时还像是一种语言武器。
笑话本质上是一种嘲讽语言。从王学泰的分析看,历史上,民间笑话可能不似朝堂笑话那样机锋四射,有的笑话土得掉渣,但是符合底层民众的话语习惯,这也是笑话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当上层建筑越来越乐于引用民间笑话时,实际上是以一种话语表达方式表示对笑话地位的承认,也是朝堂文化向底层文化靠近的积极信号。在朝堂引用民间笑话的同时,民间也会向朝堂看齐,经过精英改造的笑话剔除了糟粕,有的经过改造后被民间艺人传唱,成长为新的舞台艺术。
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笑话同样来源于生活。回溯笑话的历史不难看出,笑话从当初的讽刺他者,到今天已经出现截然不同的分野。伴随文明进步的足音,笑话生存空间越来越大,但笑话的嘲讽反倒更注重分寸了。特别是那些舞台表演,为避免观众的不适反感,更多时候采取的是自嘲,即便是对他者的嘲讽,常常也会明讽实褒。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最佳分辨率:1024 -
最佳分辨率:1024 -  设为首页 -
设为首页 - 
